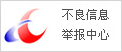鐵火鉗
像年邁得站不穩(wěn)的長者,依著人間煙火,看一日三餐灶膛的烈焰,是如何將苦難的日子一一融化。如果烈焰的火力不足,鐵火鉗在祖母的手里,張開雙臂,擁抱起柴把,向冷鍋熱灶的內(nèi)心伸去。
只要泥土壘起的灶臺還在,那些斑駁的歲月即使跑得再遠,鄉(xiāng)間瓦礫上的炊煙也能將它們纏住,牽回到我們的記憶中。當(dāng)祖母俯下身子,看灶膛的火焰時,火光映紅了祖母的臉頰。她把鐵火鉗斜靠在灶門口,起身,抖抖圍裙上的柴屑,然后走到灶臺之上,捏起鍋鏟,把五谷雜糧翻出有滋有味的生活。
祖母的手粗糙。她拿鐵火鉗的時候,動作遲鈍,如用一種慢鏡頭在詮釋:鄉(xiāng)村的飯食來之不易。當(dāng)她把柴禾下的一粒星火,用鐵火鉗挑燃成滿灶膛的火焰時,曾經(jīng)有那么一瞬,濃濃的炊煙沿著煙囪,在屋宇上裊裊升起。屋里屋外,如此飽滿的畫面,是關(guān)于“家”的最貼切的油畫構(gòu)圖。
鐵火鉗很少走出過廳堂,仿佛與生俱來就是深入廚房的什物,像舊社會農(nóng)村眾多的女性,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在幕后,默默無聞地做著自己本分的活計。因此,祖母總是善待鐵火鉗,即使鐵火鉗倒了,祖母也要將它扶起來,靠在灶前。鐵火鉗站得有些謙卑,不敢獨立。在柴禾的王國里,鐵火鉗總是與它們探討著生米怎樣才能煮成熟飯的問題。縱有荊棘相阻,祖母的老手難以介入,鐵火鉗會挺身而出,以一種絕不后悔的姿態(tài),將荊棘送進灶膛。
米飯香了,祖母用鐵火鉗動動灶內(nèi)的火星,烤出的焦黃的鍋巴被遠行的孩子帶在了背包里,帶到了異鄉(xiāng)。鐵火鉗默不作聲,像臨行前送別的祖母。只是在那些離別后的日子里,它以升起炊煙這種特別的方式,牽掛著你。我最初離開村莊的那回,背包里塞滿了鍋巴,還有被鐵火鉗從灶膛里掏出的幾個燒好的山芋。鐵火鉗將滾燙的山芋掏到灶門口,祖母用長滿老繭的左手接住,磕磕山芋表面的柴灰,然后塞在我的側(cè)包里。她所做的這些,鐵火鉗安靜地凝視著,看即將從農(nóng)村走出的孩子,是如何背起這份沉重的離鄉(xiāng)背包。
子孫是村莊的延續(xù)。柴禾年年在野外生長,年年被祖母砍回,日日被鐵火鉗塞進灶里。這一塞,就塞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光陰。祖母走了,接過鐵火鉗的母親如今也走了。我蝸居在城里,這個家的一日三餐,全部是用液化氣煮熟的食物,兒時飯食的香味現(xiàn)已蕩然無存。偶爾,我們邊吃邊生懷念,懷念那種樸素的詩意和許多難忘的場景,可惜這一切都回不去了。老家,灶臺冷卻,靜置在日子深處的鐵火鉗,不知是否依舊孤零零地依在那里。
作者:石澤豐
熱點圖片
- 頭條新聞
- 新聞推薦
最新專題

- 強國必先強教,強教必先強師。今年9月10日是我國第41個教師節(jié),主題是“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,譜寫教育強國建設(shè)華章”。